提问者 孙小宁
答卷者 陕西摄影群体渭河流域考察部分成员

2021年,我在朋友圈看到陕西摄影家在分享一本新的摄影图册,立马被它吸引。这之后蒙摄影家石宝琇先生相赠这本《渭河流域文化摄影考察30年》,有了一次从容地对一条河的阅读。边看边赞,不仅因为这是我从小就无比熟悉的,还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国内还没有一条河,能被同一群摄影人持续三十年跟踪、拍摄并书写,从源头到汇入黄河处。其中那些充满田野调查意识与人文观照的影像,因此横跨了渭河生态的三十年(1989—2019)。这群摄影人大部分都属于著名的“陕西纪实摄影”群体,之前在这个摄影领域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围绕着这条母亲河所进行的考察,后来也一直伴随着他们的摄影事业在深入,并各自开出了丰硕的果实。即使不是同饮一条河长大的人,也会对这个壮阔的历程产生钦佩与探究之心。因为每一条母亲河,都值得这样被记录。
这个提问与回答,就基于这样的背景产生。
宝鸡峡里渭河的小支流 石宝琇 摄
壹 渭河考察,从源头探起
问:
这本图册收到后发现,它比想象中还要厚重,每一张影像都带着沉甸甸的岁月意味,也真的记录了一条河的前世今生。回到考察的源头,1989年,就一条河做一次全方位的人文考察,这种意识,整个中国应该还是很少吧?是什么样的契机促成了这样的想法。
邱晓明:那是1989年初的春节期间,陕西摄影群体举办的《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落下帷幕之后,宝鸡的摄影圈一伙,有我、石宝琇、李胜利、白涛、刘宗昉、冯晓伟、吴佑民、董志云等聚会说事。我提出新议题,即成立“文化摄影研究会”,建议宝鸡群体应该转入文化摄影了。为什么叫“文化摄影”?因为在当年国内还没有产生“人文摄影”的概念。
渭河流域图 石宝琇 绘
紧接着,我又有了创立“图片库”的想法。当时我和石宝琇商量,划分了很多科目,比如中国西部的地形、地貌、地质;植被、物产;民俗、民风、民居;风味饮食……应该说在当时国内,这还是一个比较超前的计划哩。随后,“中国西部文化摄影研究会”就成立了。1989年6月8日,作为研究会第一次行动,一行8人组成的“文化摄影考察队”从宝鸡市的渭河桥头出发,开始了15天的渭河流域文化考察活动。很快,侯登科从临潼匆匆赶来,于是8人变9人。大家风雨兼程,一路经过千阳、陇县、张家川、清水、天水、秦安、甘谷、武山、陇西,最后抵达渭河的源头渭源……
1989年6月9日 渭河“文化摄影考察队”成员在武山县华盖寺附近的红砂崖下合影。从右至左:吴佑民、白涛、刘宗昉、冯晓伟、李胜利、邱晓明、任建坤(司机)、石宝琇。 侯登科 摄
问:
那在考察之初,关于这条河要考察什么,走什么样的路线,有明确设定吗?这个路线如果今天有人还想依着续走,还能走通吗?
刘宗昉:有较为明晰的思路。行前好几个晚上大家都在一起聚会讨论、研究线路,包括落实每个人具体都拍什么。像我就是以拍村庄环境、房屋等为主。最后形成的方案很详实,往返的考察线路基本没有变化,一直按照既定方针履行。只是中间车子出了几次问题,耽误了一点时间。今天有人想依着续走,可以顺利走通,只是一路情景变化大得很了。
李胜利:当初我们的准备过程很长,从1989年春节开始,一直到6月出发。因为这种摄影考察,和以往的“信天游”式的“扫街”和“采风”,是截然不同的。之前,除了完成什么主题性展览或者画册,必须围绕某一内容拍摄之外,其他都是“搂草打兔子”,“拾到篮里都是菜”,自由自在的,从来不难为自己。这回可好了,一个个地给自己套上了“枷锁”。因为渭河考察,其实就是后来人们说的“田野调查”,是带有强烈目的性、逻辑性的摄影活动。它内容复杂、琐碎,分工很细。比如,有人以拍摄建筑、村落、商铺为主;有人以拍摄民居、家庭生活和摆设为主;有人以拍摄田野、庄稼、耕作、家畜、农具为主;有人以拍摄市场、人物活动、人物肖像、群像为主……还得有详细的文字记录。
1989年6月 陇西县濒临渭河的山顶 李胜利 摄
对于每位队员拍摄的侧重,当然也会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和爱好来分派。但项目那么多,也很难摊派,就只好各自“认购”了。我领的是“风景”、“人物”、“集市”等。后来,我也一直热衷于拍摄农村集市、庙会、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或许和当年的分派有关系?积攒的形象多了,我就出了一本《关中父老》的画册,其中的人物形象都来自渭河中下游区域。
贰 文献是概括的粗线条的有些疑问随着调查深入才有答案
问:
那提前所做的功课里,应该也有对文献中渭河记载的阅读吧?将文献与沿途情况再做对比梳理,有什么新体会、新发现?
白涛:渭河考察是个系统工程,但在30年前对于我们第一批考察队员来说,全面考量,大部分队员还是朦朦胧胧的。还好这里有独树一帜善于接受新思想的邱晓明,有酷爱读书细研深究的石宝琇。当时虽说没有现在这么发达的互联网,但他们依然根据少有的资料制定了拍摄主线。加上几乎所有的考察队员,是傍依渭河,生于斯,长于斯,对于渭河边的芸芸众生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和直觉。平日拍摄的主题也与渭河考察息息相关。因此像那些被称为防盗匪的土围子,灶房、大门的开向等都定格在了胶片当中。
1989年 岐山县蔡家坡镇的渭河渡口 白涛 摄
渭河上下的沧桑风情和文化现象,其实就是人文地理学的“人地关系”,既是人对于万物的态度,也是朴实而真诚的价值观。30年当中我们多次沿着渭河去考察,边拍摄、边总结,要说发现,还是有的。更主要的是,文献都是概括的、粗线条的。像为什么甘肃的麦客像候鸟一样每年都来陕西割麦?为什么土堡遍布渭河流域上下?为什么甘肃的渭河流域神庙林立,供奉的有伏羲,还有佛、道等各路神仙?这些随着调查拍摄的深入,答案才一一露出。都和当地的地理地貌、环境气候、贫穷有关。从关中平原去甘肃,有些地方不到现场根本不知贫穷是何物,这些也是文献里所没有的。当然经过30多年发展,很多地方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问:
除了考察、拍照,沿途还有什么特别难忘?
白涛:当时我们的工资都不足百元,考察中大多住的都是车马店或最便宜的招待所,通常8人一间房,每天每间房费大概5元左右。每天早、晚饭在小店打发,无非是稀饭、馒头、面条。中午饭,仅仅以烧饼充饥。记得有一次在陇西时买了一次陇西腊肉夹馍,大家就像过大年一样,在山巅的公路边大吃一顿,至今那股香艳的味道,还记得清楚极了。
走渭河考察,实行的是所有花费“AA制”,吃、住、行,还包括车的汽油费。这一例制一直延续至今。这也是大家能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做好一件事的基础之一。
再就是那时胶卷金贵、有限,大家惜卷如金,“不见鬼子不挂弦”。后来我们都退休了,每个人再次更新了设备,随后加入的新队员再次壮大了这支队伍,也带来自己购置的更精良的设备,这也给渭河考察带来了勃勃生气。
1990年岐山县高店镇渭河滩捞砂 白涛 摄
叁 渭河就是这样一条身价不凡的河流
问:
可能每一个在渭河水长大的人(也包括我)都觉得这条河不陌生,但依着这本厚图册从源头读起,会发现上中下游非常不一样。直观感受是,越往上游走,农耕文明的特色更明显,元素也更多元。尤其那些人物肖像,都让我想到“高古”一词。“秦”这个字眼,是不是一下子从陕西给拓展出去了。也相信此行,你们对“秦”字的理解,比没走过这一遭的人深刻。不妨说一说。
石宝琇:的确是这样,一条800多公里长的河流,它的上下游的自然、人文情景是不同的,但也有一致的存在因素。不经过实地考察,一些具体的微妙的差异,是很难知晓的。
人常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摇篮,而渭河正是关系到这古老摇篮摆动的中轴部分。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黄河从秦晋之间穿过南下,当进入晋陕豫交接处的潼关急转向东时,由西淌来的渭河便直直切入这条大河,形成了渭河和黄河的横向轴线。这就是中国古文化之轴,世界闻名的古都长安、咸阳、洛阳、安阳、开封都在这条轴线上被串联。
经过30年渭河上下求索,逐渐知道了更多属于渭河的故事。原来它和历史上秦国、秦朝的演进、消亡息息相关。
2014年2月 陇县关山古道旁的牧马场 石宝琇 摄
我在2004年,曾租了一辆车,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专门来了一次“寻秦记”。终于得出结论,渭河若有外号,应该叫“秦河”。且看,渭河造就的关中平原又称“秦中”,这“秦中”又有好多与“秦”字相关联的事物,比如山有“秦岭”,地有“秦川”,丘有“秦陵”,墙有“秦长城”,字有“秦篆”,菜有“秦椒”……而上游天水一带在古代被称作“秦州”,还有秦安县、秦亭乡、秦家塬村。从渭河入黄口,一直到渭河源头,不论甘陕的哪个县市,哪个乡镇,所有原居民,都喜好“秦腔”……这“秦”字堪称渭河流域的精神所在。
在陕西地理的传统叙述里,关中,即指“八百里秦川”,渭河中下游贯通其间,西安据其中。下游的渭南为“东府”,中游的宝鸡是“西府”,又称之“西秦”,因为先秦曾以雍为都。雍,即现在的凤翔一带,还应该包括鸣凤的“岐山”、扶风、武功。
要说起渭河上下游的相同之处,的确发现不少有趣的现象。刚刚说到上下游同一个戏种“秦腔”;还有饮食口味都趋向“酸辣”;房子多是一边盖的“厦子”;防盗防土匪的“堡子”皆有……
迥然相异的,也不少。比如长相方面,上游的原住民和下游的关中东府人,差异最大。日常言语的发音、节奏、口型也有很大差别。体型上,上游人比下游人腿和胳臂要长,尤其妇女。再者,上游农家的耕作极其细致,因为降水少,全靠精耕细作来弥补天然不足。用具上也有区别,比如背篓,下游的平原很少见到,而中游的宝鸡山区开始出现。到了上游,山峦起伏不绝,使用背篓变得极其普遍了。而且背篓也出现了尖底的,于是有传说,是秦始皇修长城时,怕劳役背土石偷懒,就让人发明这负重途中难以置地休歇的尖尖底背篓。
问:
上游还是古丝绸之路必经地,就你们眼中所见,和丝绸之路相关的风物有哪些?具体到渭河周边,还有哪些文明遗存其实非常值得一看?
冯晓伟:渭河,与古代的丝绸之路的走向和主要路线,几乎是同一的。因为在古代开辟道路能力低下,只有依赖河谷的平坦和水源,才能顺利远程行旅。
这本《渭河流域文化摄影考察30年》有写:“开拓这丝绸之路的先锋,应该是来自西方印度的佛教传经者,然后是去西天取经的中国僧侣。当然,僧侣只是少数派的意识形态精英,而真正把渭河流域开拓为东西方往来坦途的,还是靠务实派的商旅和军旅这两大主力。”在溯源的考察过程中,我们发现渭河主河道,主要支流,都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比如从首阳山到木梯寺、拉稍寺、华盖寺,再到大象山、麦积山,人们崇敬的佛、神、圣、贤的偶像都被安置在野山幽静的去处。尤其顺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原的佛,在渭河上游的地位最显赫。大自然营造渭河为相对畅顺的通道,人类借势开拓了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西天的佛教,便顺着古道来了。佛教的信徒们在渭河两边为佛造像,随之而来的是国粹道教。佛山的周围遍布中国诸神的殿,其中还有许多人杰的庙堂,比如伏羲、女娲、大禹、周公、姜太公、医圣孙思邈……而在渭河支流泾河流域,又有道教的西王母宫、崆峒山,以及彬县大佛寺。另一条支流千河流域,则有道教的龙门洞、灵山大庙,还有8000多年前的秦安县大地湾、宝鸡金陵河畔的北首岭古文化遗址。

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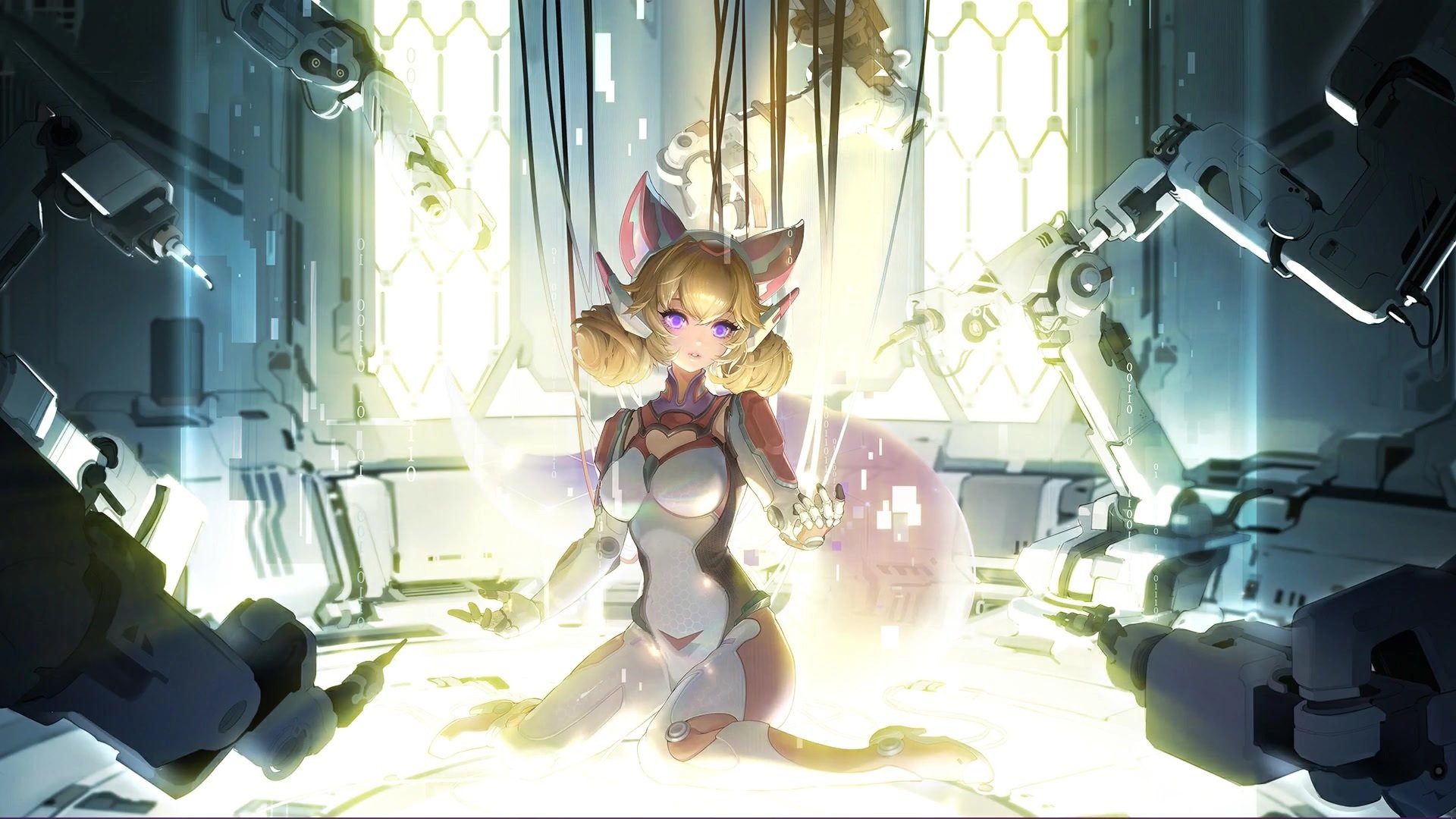
常有一句话,“人不能同时踏入同一条河流。”世事瞬息万变,你们眼中的渭河也是。是不是像白涛所摄的《1990年岐山县高店镇渭河滩农民捞砂》这样的生活图景,再也看不到了。另外还有哪些消逝的风物?
白涛:我们是听着渭河的波涛长大的。1968年我插队下乡就在五丈原公社(现高店镇)西星大队,紧邻渭河。那时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富裕生产队,每十分工8角多钱,但劳动强度十分之大。春天在滩地种水稻,冬天修河堤,为了方便南来北往的村民,我们村在渭河上有了自己的渡船,本村人免费,其他人收费5分钱。1970年渭河上修建了大桥,渡船也转卖给了下游偏僻的渡口。后来桥越修越多,短短十余公里竟然就有四五座桥,因此我拍的眉县河边老渡船,也就成了绝唱。
1989年6月 渭源县城郊村的老人家 李胜利 摄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各种基建热火朝天,渭河捞砂成了农民的致富路,骡子、架子车是主要工具。后来随着河道管理的规范,捞砂图也成为了最后的图像。
河还是那条河,波涛却没有了。我下乡时曾拉石头的渭河支流石头河,也就是历史上的“褒斜古道”上的斜水,在1970年代满河床还是大石头密密麻麻。如今,连找一块西瓜大的石头都难。而沿着河边的稻子,早就变成了一年二收的旱地。要说消逝,这些都是……
肆 摄影的自觉,生态的自觉
问:
现在再重看这个考察团成员名单,几乎都是陕西纪实摄影群体成员。想知道,是否这个群体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产生于这次考察当中。比如侯登科、胡武功“麦客”系列,以及白涛他们不同的乡土题材系列?
胡武功:1986年陕西群体发起、组织首届全国摄影美学研讨会,并在会议期间举办《西北风摄影展》,同年九月第10期《现代摄影》以“陕西群体”称谓作报道,以此“陕西摄影群体”正式走入中国摄坛。1987年又成功举办了《艰巨历程》全国摄影公开赛,1989年6月在日本成功举办首次巡回展。这一系列活动,对于陕西群体来说检验了经过数年学习与实践探索出的摄影理念,这就是“摄影必须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人性”。
那时,群体成员都有一种危机感和焦虑感:数千年一以贯之的生存方式、千年不变的农耕文明及历史遗存将很快消失。于是,由邱晓明提议用摄影的方式系统地考察母亲河——渭河,大家一拍即合。系统考察之前,群体的各个成员都完成了观念的转型,抛弃了图解式的僵化拍摄模式,拍摄了许多最底层民众生存状态及其人文活动的照片,而经过考察渭河摄影活动,群体成员更加学习和领悟了“田野调查”方法。这在石宝琇后来的一系列拍摄和编辑工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侯登科2000年出版《麦客》时曾专程回访麦客家乡补写文字,应当说也是受益于渭河考察和“田野”方法的启示。
我于1990年春天,参加了第二拨渭河考察。路线是从西安出发,经渭南、大荔、合阳、澄城、蒲城、韩城,过华县、华阴,到渭河入黄河的潼关结束考察。经过这次实践,不但对渭河平原的关中大地有了较清晰的认知,更多地了解了它的历史遗存、人文精神和民风民情。对后来完成《藏着的关中》专著、《蜀道》专题、《告别老西安》和与侯登科、邱晓明合作的《四方城》等积累了经验。
1996年西安市明城墙顺城巷 胡武功 摄
群体考察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群拍”现象,使一些影像重叠雷同。但成员之间的激励、启发和有意识的交流,也多有积极意义。从实际效果来看,每个成员的作品最终都显现出各自的特点。应该说,渭河考察在陕西摄影群体形成与成长中是一次不能忽视的重要事件,这在30多年前的中国摄影界还是鲜见的现象。
问:
虽然有组织的考察是在1989年、1990年,2018年又有一次。但是事实上,这里收录的图片,远不止于这几次所拍。所以这是个历时性成果。当然,你们见证了这条河,这条河也见证了你们。就这个意义上,想让诸多摄影大咖们说一说,这些年不断拍摄实践,对摄影、对渭河作为母亲河的理解,有什么变化?
石宝琇:确如你所说,30年中,有组织的、群体行动,是三到四次。但保不住谁一时“心血来潮”,就会溯源或者顺流,独行上路。就我所知,邱晓明、胡武功、白涛、侯登科、李胜利、刘宗昉、冯晓伟等,都曾不止一次地单独行动过。其中次数最多的,应该数白涛和胡武功。我也曾借着做“唐蕃古道”“隋炀帝西行”“寻秦记”等人文地理题材,又把渭河中上游走了三个来回。
起先,只是比较纯粹地溯源,寻梦一般地去追溯这一条和中华万千年历史密切相关的河流的不俗精髓究竟藏在哪里?后来的拍摄活动,虽然目的不一定都是那么明晰,但死死盯住渭河两岸百姓的生态、命运,牢牢守住这一方水土的春夏秋冬,紧紧跟着乡亲们的步履,去过大年、去闹春、去赶集、赴庙会……还有婚、丧、寿、诞的事儿一样不落下。
古代绘画曾有《清明上河图》,其实我们30年的拍摄,足够组合一幅渭河芸芸众生过日子的长卷。
2019年11月1日早上, 当年的老队员邱晓明、李胜利、刘宗昉、冯晓伟、石宝琇,和新队员杨司令、王尚勋、张锋等八人,从宝鸡峡东口出发,重蹈三十年的渭河源考察之路。 张锋 摄
我们这些渭河考察参与者,大多数土生土长,也就是说,是看着渭河水长大的。它和我们的关系,那的确是不离不弃。朝代更迭,身不由己。替天行道,为民请命,尽是革命者的理想。但维护渭河的自然河流本性,却是我们这些渭河流域居民自觉的使命。
渭河和天下所有的河流一样,自古扮演着双重的角色,既有让人由衷颂扬的功德,也有让人诅咒的恶行。在旧时,人的能力有限,只有通过祈神,或者修筑堤坝,来消极对付。后来,人的威力越来越大,欲望也越来越强,渭河也出现了被人类伤害的可能。
2005年,我曾写了一篇博文,题目是《渭河死了》。说的是有一位省人大代表发出“渭河基本生态功能面临丧失”的警示。什么叫“丧失生态功能?”用通俗话讲,那就是“渭河快死了”。这是在热情追求高速度发展的现代文明大潮中,人们的任性和狂放所致。多亏人们及早警觉,之后多年中强行关闭了无数伤害渭河的造纸厂、化工厂、水泥厂、冶炼厂……如今的渭河,已经基本回复了河流的自然生态——渭河被救了。(责编:孙小宁)







